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
更新:2023-09-19 09:18:30 高考升学网几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日本在过去20经历的、以及美国和英国现在正经历的情况是,即使利率为零,人们还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们只是一味地还贷。”如果他说得没错,那么西方经济体将可能进入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下面这一点或许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东京至少还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
西方的困境令东方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当然,关于这一主题出现过多种变异,比如更具干预色彩的政府。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试验,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和印度尼赫鲁式的“”,都遭遇了惨败。
20世纪70代末,邓小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由此放弃了共产主义。1991,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因为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所言,它们的经济在同一条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现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他表示。在印度,人们深深担忧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和西方金融推动下的增长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甚至中国经济也在放缓,少数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可能出现硬着陆。
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关于政府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从金融监管到产业政策的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银行的角色。在亚洲,银行的职能通常较为狭窄,其角色是把资金引导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
亚洲或许忍不住会坚持其狭隘的模式,不仅因为这样的银行给经济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为在危机时期更容易对它们进行“围护”。自起,北京方面就发现,保持银行的驯服、并通过它们以固定利率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亚洲各国政府已经看到了放松银行管制的危害,它们为什么还要向“更复杂”的西方银行模式转变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这样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中国应该继续走开放经济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导的银行在根据政府指令分配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陷入麻烦——也确实陷入了麻烦。亚洲开发银行的李昌庸表示,让亚洲经济体放弃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是错误的建议。“如果不飞,就不会有事故,”他举了最西方灾难的例子。“西方有许多飞机,所以会有坠机事件。那么,我们应该不要飞机吗?”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它鼓励创新、无所不能,并且促进个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样明显。它非常多变、对员工残酷,并且在经济低迷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他更偏爱北欧的高税收、相对等、较少发生盛衰循环的制度。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和韩国有点接这一模式。
在受够了西方的说教后,亚洲人现在或许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困境中获得一些愉悦。但亚洲唯一接美国生活水的国家,就是20世纪80代末、90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巩固优势地位之前,经济就陷入了停滞。中国建立了在贫穷国家实现高增长的机制,但它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在不对其进行“大修”的情况下,赶上西方的生活水。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内,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预,也可以减少计划。在亚洲许多国家,这些政策选择尚有待讨论。不过,在选择的压力猛然增大时,大多数人都信服资本主义,并且,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的国家,将只能依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市场机制和激励的力量——确实得到显现,”李昌庸表示。“一些资本主义的要素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有幽默感的人 事业更成功2023-09-13 17:39:40
大学生求职 职业幸福感不光来自“钱”2023-09-15 00:50:56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在安徽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2025-05-23 16:27:35
浙江财经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2025-05-23 16:26:21
江苏高考排名在70900的物理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24:57
四川高考排名在193450的文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23:34
辽宁高考391分能上的公办专科学校有哪些2025-05-23 16:22:06
南京邮电大学重庆录取分数线及招生人数 附-2020最低位次排名2025-05-23 16:20:52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云南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2025-05-23 16:19:42
浙江理工大学和上海电机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2025-05-23 16:18:27
浙江外国语学院和临沂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2025-05-23 16:17:06
河南高考排名在228150的理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15:34
重庆高考排名在19500的历史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14:12
西安邮电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2025-05-23 16:12:48
有幽默感的人 事业更成功2023-09-13 17:39:40
大学生求职 职业幸福感不光来自“钱”2023-09-15 00:50:56
最新图文

大学生生活规划及目标设定
时间:2023-09-18 13:0:08
大学生个人未来工作计划范
时间:2023-09-15 14:0:45
大学生个人未来职业生涯计
时间:2023-09-16 08:0:36
大学生未来计划与目标范文
时间:2023-09-17 16:0:44 有幽默感的人 事业更成功
有幽默感的人 事业更成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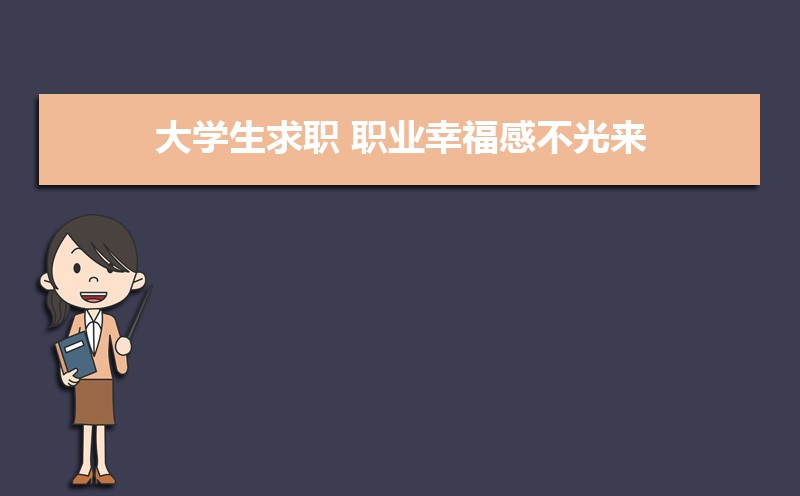 大学生求职 职业幸福感不光来自“钱”
大学生求职 职业幸福感不光来自“钱”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在安徽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在安徽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 浙江财经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浙江财经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江苏高考排名在70900的物理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江苏高考排名在70900的物理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四川高考排名在193450的文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四川高考排名在193450的文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辽宁高考391分能上的公办专科学校有哪些
辽宁高考391分能上的公办专科学校有哪些 南京邮电大学重庆录取分数线及招生人数 附-2020最低位次排名
南京邮电大学重庆录取分数线及招生人数 附-2020最低位次排名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云南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云南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 浙江理工大学和上海电机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浙江理工大学和上海电机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浙江外国语学院和临沂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浙江外国语学院和临沂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河南高考排名在228150的理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河南高考排名在228150的理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重庆高考排名在19500的历史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重庆高考排名在19500的历史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 西安邮电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
西安邮电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